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经过7次政府改革,所有重大战术变革都出现在政府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上。 无论党的事业中心是向经济建设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加入世贸组织。
从纵深看,中国这30多年的政府改革,每次比较的阶段性任务不同,侧重点有很大不同,但始终如一的主线是转变职能促进经济增长。 其客观结果是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全能型政府分化为政府和市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公权力寻找边界的过程。

这也使政府改革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 现代国家的基本重要意义之一是公权力需要边界,其次是民主化和法治化。
在中国,要想完全明确权力和市场的界限,狭义的政府改革——机构改革和将政府职能变为第一副本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扩大到执政党、司法体系等的改革。
2008年以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增大了
自1982年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机构改革以来,中国在31年间进行了7次政府改革。 要点是机构改革,或者是政府职能转变,但一贯的主线是促进经济增长。
“这是30年来七次政府改革的规律之一,也是中国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国务院政府职能转变专家组成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说。
从七次政府改革的首要背景来看,1982年第一次改革的首要背景是政治背景。 除了党的事业中心从政治转向经济建设,1988年的改革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背景外,其他五次政府改革的首要背景是经济因素。
这七次政府改革,虽因成果而异——1982年改革开创了干部人事制度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历史,1988年改革首次提出“政府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关键”,1993年改革则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表示,这几次政府改革促进了政府和机关职能的转变,略微剥离了政府的非公共职能,使政府向单纯行使公共权威、提供公共产品的机构转型,使公司、事业单位向单纯的经济或社会实体转变,不再承担全能主义政治基层组织的职能

具体来说,第一,通过几次改革,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经营公司的规模和程度大幅下降,大部分国务院部委都变成了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 特别是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国有资产。
“经过这次改革,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管理国有资产两方面的作用在制度上有了区别。 换言之,将政府区别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资本的所有者或产品的生产者两者的作用。 ”李强解释道。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或减去现有政府部门,根据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快速发展的诉求,增设一些以提供行业公共产品为职能的政府机构,处理所谓政府“短缺”的问题,如安监局、食品药品监督委员会。
第三,通过几次税制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共权力的行使越来越依赖公共财政的支持,越来越少依赖各种形式的资金收付。
第四,公司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通过一系列国有公司的分类改革,国有公司原有的单位制特征大大削弱,国有公司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大幅减少,逐渐转变为能够根据市场经济基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单纯生产者。
但是,前后7次、持续30多年的政府改革,并不意味着整理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够,过多参与微观经济运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然薄弱。 部门间职责的交叉、责任与责任的背离、效率不高的问题依然突出; 对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的行政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权力私欲、贪污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政府全面、准确地履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李强说。

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将政府职能变为核心复制的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放缓,在某些方面发生了逆转,政府权力扩大成为普遍现象。 特别是2008年以后,随着南方冻结、5·12地震、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政府开始直接踢球”。

“这是不得已的历史选择,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变大,在19个领域产生了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 ”宋世明说。 这也是需要继续推进政府改革的理由之一。
机构改革不应该频繁进行
宋世明分析认为,从基本布局看,本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已尘埃落定,同时项目化、有时间要求、责无旁贷。 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组织改革不能过于频繁——有人认为,30年来的政府改革都是五年一次的调整,迄今为止已经如此频繁,应该放眼长远。 而且,因为经过这么多机构改革,其边际效用明显减少,改革的空间和空之间已经非常小了。 25个部委不能简单地说比15个部委好,部委的职责涵盖所有行业,职责不交叉也不能贯彻。

当然,从长期来看,不排除在盐业、烟草等稍有“政企分开”不顺的行业会进行组织改革。
关于曾经呼吁设立改革委员会的问题,从高层的态度来看,为了决定咨询,倾向于鼓励智库迅速发展。
李强说,进一步取消合并部委被认为“意义已经不大,是个技术问题”,转变政府职能至关重要。
因为,职能转变涉及政府的定位,政府与老百姓、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首先决定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的边界在哪里、以及要在什么样的机构做什么、需要多少资源。 否则,机构的设置就没有根据。
实际上,在1988年的政府改革中,提出了“政府职能的转换”。 “但是,这次改革只是‘指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这要等到十年后的1998年政府改革。 ”宋世明说。
比起1998年政府改革取消10个部委的大动作,之后的目标——政府职能的转换——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 相反,15年后的一年,当舆论预计政府改革将在机构改革中制造“大规模复制”时,政府职能转变就成为了重要因素。
那么,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这一政府职能转变,今后还会有那些改革措施吗?
垄断行业的技术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最困难的部分
“在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光是行政审查制度的改革这一点就没有头绪。 ”据宋世明介绍,中央政府撤销和下放的1000件以上的审批权目前也只动用了200件以上。
尽管如此,他认为,未来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推进垄断行业的技术改革。 也就是说,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深化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让价格在资源配置中发扬风格,管理地方融资平台。
在1998年的那次政府改革中,几乎没有反复取消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后,朱镕基总理任内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之后1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2008年以后的中央经济刺激政策下,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停止了,而且由于垄断地位以及土地和资金方面的政策特点包围着,“国退民进”的投诉不断。

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们表示,垄断行业的技术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最困难的部分,但不迈出这一步,就无法彻底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资源性产品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要素,但这一领域的价格改革至今尚未完成。 政府仍然牢牢控制着水、电、油气、煤炭等基础性资源产品的定价,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的谈判筹码。 因为这也将成为未来政府职能转变中必须克服的“山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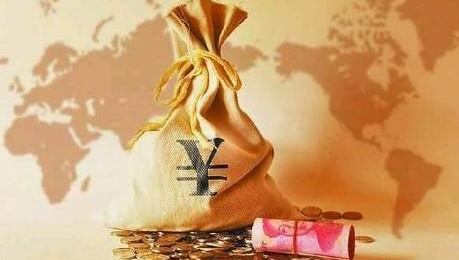
中国的金融体制被诟病已久,但由于其改革风险较大,一直被拖延。 今年夏天,随着贷款利率市场化政策出台,上海自贸区预计汇率市场化、人民资本项下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并放松,金融改革值得期待。
关于地方融资平台,这是我国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建设型政府深入介入市场的典型形式,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目标是使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如果管理地方融资平台,无论地方如何早点工作,都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会变得合理。 ”宋世明说。
另外,土地、投资批准、生产能力指标管理也被认为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必须处理的问题。
而且,政府不仅要退出一点经济事务,政府职能转变也要求政府在一点行业承担监管责任,从前监管向事件中、后监管转变。
在明确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李强首先认为政府应该退出一点点的社会事务,其次必须培养社会组织的成长。
因为,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基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组织的成长。 否则,就不能转用政府的职能。 社会上没有承担者,要实现政府机构改革的既定目标并不容易。 这还与事业单位的配套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培养密切相关。
李强说,政府必须非常明确。 那些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些不是。 “不仅是中央,省、市、县、甚至小街,都应该确认这些事情应该管理,不应该管理。”
不能只是“政府改革”
“政府这个词,我曾专门研究过。 其含义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发生了变化。 80年代,人们把所有公权力机关——党、政、人大、政协和司法机关——看作政府,但现在政府指的是狭义的行政部门。 ”李强说。
这是因为,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贴近“政府改革”——行政部门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还不够,需要明确整体公权力机构——执政党、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与市场的关系。
标题:“政府改革30年:垄断业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最难部分”
地址:http://www.s-erp.net//sdcj/262.html











